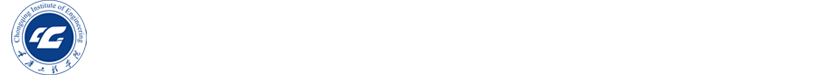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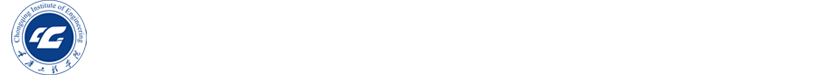
夏商周青铜面具:镌刻在铜器上的时代记忆
夏商周时期于中国青铜时代占据核心地位,青铜器承载深厚文化底蕴,青铜面具更是独树一帜。其在多地的出土,为剖析当时宗教、社会、艺术与文化交流提供关键线索,极具学术与文化研究价值。
夏代青铜面具:
夏代开启青铜时代,青铜面具发现稀少。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(图一),虽形态特殊,但在兽面勾勒上采用简洁几何形与线条,初步展现青铜面具造型雏形。经放射性碳定年等技术测定,其年代约处于夏代纪年范畴,为后续研究提供年代基准。范铸法在其制作中的运用,经金相分析可见工艺已具一定水准,为商周青铜工艺发展奠定基石(参考《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研究》)。
夏代兽面铜牌饰以抽象几何造型与简洁线条勾勒兽面,如绿松石镶嵌构成的兽目、鼻梁等元素,简洁而神秘,凸显古朴原始韵味,或源于早期图腾与宗教信仰,是夏代精神文化在艺术领域的初步映射。

图一: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
商代青铜面具:
商代青铜面具出土丰富。三星堆青铜(图二)纵目面具震撼世人,其宽 138 厘米、纵径 85 厘米、高 66 厘米,造型极度夸张。方脸、粗眉、柱状凸眼、宽鼻、阔嘴、尖耳等特征,在《三星堆考古研究》中被认为可能与古蜀神话或宗教意象紧密相连。此外,河南安阳殷墟等地也有不同尺寸面具出土,小者如真人面部大小,大者超乎寻常,反映出商代青铜面具用途与风格的多样性,与当时社会文化生态密切关。

图二: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
特点及用途:商代青铜面具造型夸张,三星堆纵目面具的奇异五官塑造突破现实,超大尺寸与独特形态营造强烈神秘氛围。从艺术风格演变视角,其反映商代宗教狂热下对神灵、超自然力量的独特想象,在青铜艺术造型创新进程中影响深远,开启独特审美风尚(参考《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史》)。
文化意义:反映了商代人对神灵和祖先的高度崇拜,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,同时也体现了当时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独特的审美观念,是研究商代宗教、文化、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西周青铜面具:
西周应国铜人面具(图三)具代表性,高 18 厘米、宽 14.2 厘米、厚 3.7 厘米、重 447 克,五官刻画细腻写实。从西周墓葬考古发掘报告来看,此类面具于车马坑频繁现身,其作为盾饰、车马饰的功能,与西周军事活动紧密交织,彰显军事文化特色,体现西周青铜文化对商代的传承变革,于青铜器功能拓展意义深远。

图三:西周应国铜人面具
特点及用途:相较于商代,西周青铜面具在造型上更加写实,开始注重对人物面部细节的刻画。这时期作为盾饰和车马饰的青铜面具大量出现,多出土于车马坑中,作用一方面是作为人或马面部的防卫,另一方面也是祈求神灵的保佑和威慑敌人。
文化意义:体现了西周时期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”中对“戎”的重视,也反映了当时的战争文化和人们对战争中安全与胜利的祈求,同时也显示了西周在继承商代青铜文化基础上的发展和演变。
制作工艺及文化交流:
夏商周青铜面具皆以范铸法为基。夏代范铸工艺在铜牌饰体现初步规范,从模具制作到青铜浇铸、修整,流程虽简但奠定工艺走向。商代工艺精进,多范组合复杂造型,如三星堆面具眼部、耳部单独制范再铸接,经 X 射线探伤技术揭示内部结构,展现高超分铸、铸接技艺。西周传承创新,在写实造型中优化范铸精度与纹饰雕刻,体现工艺传承革新关系,于冶金史研究为青铜铸造关键环节(参考《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史》)。
商代三星堆面具与中原文化,虽造型独特,但在青铜材质、部分纹饰母题上有共通,中原云雷纹、饕餮纹变体见于三星堆面具,显示文化传播融合。西周时期,随军事征伐、分封等活动,青铜面具文化随青铜器传播至边疆,融合当地文化催生新样式,于文化交流史中见证华夏文化多元一体进程,促进文化融合创新。
结论:
夏商周青铜面具贯穿青铜时代文化、艺术、工艺与交流脉络。从夏代奠基、商代繁盛到西周变革,其为探究古代文明关键窗口,承载宗教、社会、审美多元信息,见证文化交流融合,持续推动学界对该时期深度研究,未来新考古成果将拓展其研究广度深度,深化古代文明认知体系。
参考文献
[1] 杜金鹏.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研究[M]. 科学出版社, 2015.
[2]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. 三星堆考古研究[M]. 文物出版社, 2019.
[3] 李学勤. 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史[M]. 商务印书馆, 2013.
[4] 李伯谦. 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[M]. 科学出版社, 1998.
[5] 郑光. 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[J].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——中国·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, 2006: 104-120.
[6] 施劲松. 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[M].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
[7] 陈显丹. 三星堆文化研究[J]. 四川文物, 1990(6): 3-10.